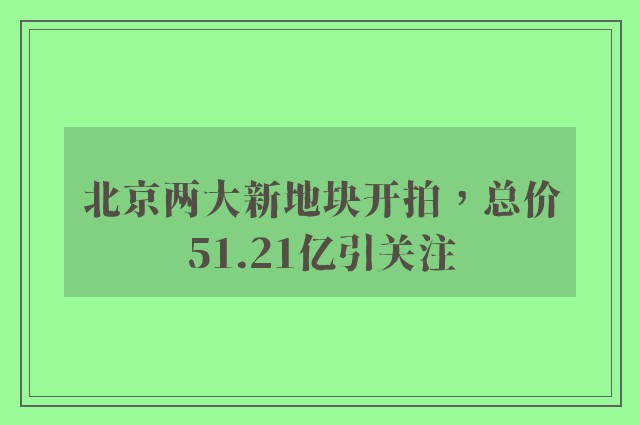杨妞花的“背景墙”
极目新闻记者 唐佳燕
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时,几十家媒体将镜头对准杨妞花。在杨妞花的背后,来自贵州的寻亲团和其他受害人默默站在她的身后,他们的愁容和红色的寻人信息组成一面特殊的背景墙。
 杨妞花被寻亲家长簇拥
杨妞花被寻亲家长簇拥
如果说杨妞花是“大女主”,她被拐后亲手复仇是故事中罕见的、明亮的一面;聚光灯外,其他受害人和贵州寻亲团则是普遍、灰暗又坚韧的一面。
采访之后,他们的面目一个个逐渐清晰浮现:有的寻亲家长为了寻子,开着贴满寻子信息的面包车,一边卖棉花糖作为路费;有的已头发花白,在镜头前只乞求能最后见儿女一面。有的受害人,在孩子丢失后大半生守着擦鞋摊,已经年迈却依然无法与子女团圆;有的至今只和孩子在认亲时见过一面,认亲之后亲生骨肉却依然是陌生人。
受害人需要杨妞花的记忆,寻亲团则需要她的流量。他们把杨妞花唤作“贵州女儿”,甚至希望儿女就是杨妞花的样子,而杨妞花也不曾忘记她最坚实的后盾:开庭前一天,杨妞花一个个把寻亲家长拉到镜头前“直播带人”,捐出五万块作为寻人经费。妞花姐妹给经济窘迫的寻亲家长们订酒店,帮找回儿女的家属弥合亲子关系。
他们支持杨妞花,需要杨妞花,并且等待着下一个杨妞花出现。
记忆的力量
68岁的罗兴珍老了,老得经常接不到电话了,但她很庆幸,自己没有错过这一通电话:12月18日,杨妞花打电话托人告诉她,余华英案再次开庭了。第二天一早,她关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修鞋摊,踩上一双单薄的解放鞋,穿了四五层棉衣,从都匀坐警车到贵阳,“我要看到余华英死”。
一对儿女走丢的日期她记得很清楚,1996年7月2日,余华英拐走孩子的手段和拐走杨妞花相似:先是租住在附近,借着女儿和罗兴珍儿女混熟悉,趁大人不在家,将罗兴珍7岁的女儿华兰和5岁的儿子华白带走。罗兴珍到余华英的出租屋时,对方已人去楼空。
此后26年,罗兴珍守着修鞋摊,换过不知道多少张寻儿女的广告牌。丈夫全国各地打工寻子,如同大海捞针。直到2022年,杨妞花在寻亲成功后发现双亲早已含恨而亡,并决心复仇,凭借5岁时精确的记忆,提供了余华英的名字、长相等关键信息,协助公安将余华英绳之以法。
“如果不是妞花,我也不会找到家”,余华英案最后一位认亲成功的孩子谌江海决心面对镜头。
谌江海曾经恨自己的记忆,他记得自己在5岁时在游戏厅被一个女人拐走,但始终记不起那人的长相。只记得家在“太阳落山的方向”,无数次出走却记不起具体位置只能“回家”。他也很自卑,认为自己“表达能力不好”,无法向养父开口,只能将痛苦都写在日记里,直到被姐姐“偷看”,在她的支持下开始寻亲。今年余华英案重审,他接到警方通知:“你可能是被余华英拐走的”。
“妞花的记忆真的很有力量。”说到这,他红了眼睛。
 谌江海出现在镜头前受访
谌江海出现在镜头前受访
杨妞花对媒体说,和女孩不同,男孩在被拐卖后回家的道路更坎坷,年少容易因和养家不亲走上错误的道路,有的男孩在寻亲成功后也轻易脱离不了养家,或已成家、面对养老压力,有更多的顾虑,能站出来“是需要勇气的”。
陈丙连的5岁小儿子是在她摆摊时,在贵州都匀被余华英用一个冰激凌拐走的,当时没被拐走的大儿子至今仍不吃冰激凌。余华英被捕后,小儿子被找回来,但“团圆”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陈丙连说,儿子自从寻亲成功后没主动见过面,今年她想和儿媳妇视频,被儿子拒绝,她小心翼翼不敢问,“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”。罗兴珍则说,儿女认亲“只远远看过自己一眼,连声妈都没叫”,转头又说,自己不恨儿女,只恨余华英。
 陈丙连
陈丙连
杨妞花则努力成为缝合亲子关系的纽带,她特意在镜头前解释,罗兴珍在河北邯郸的儿女定期会给她汇款,只是她年纪大,记忆不清楚了,两人其实很孝顺,只是各自成家后生活条件有限,不应苛责被拐的子女;陈丙连也记得,杨妞花今年特意将她和儿子儿媳妇叫到杨妞花家里相见,“我见到儿媳妇很喜欢,对我也很好”。杨妞花回贵州时,还来都匀看过她,给她带礼物,“比我亲生的还亲”。
“要是我的儿子也像妞花,就好咯”,陈丙连叹口气说,自己也亏欠儿子,“毕竟二十多年不在(儿子)身边。”
12月19日,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,余华英拐卖的12个家庭中,杨妞花和其他10个家庭均出席,但被拐儿童中只有杨妞花和谌江海2人到场。开庭前,杨妞花表示,自己这次在法庭上将会为其他10个家庭“代言”,“我希望把其他受害人的故事讲出来,让余华英看到,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。”
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被起诉拐卖11名儿童,重审追加另外6名。重审二审结束后,杨妞花案代理律师王文广说,6次开庭,余华英始终辩解自己不是主犯,余华英目前被控拐卖17名儿童,无一人是她主动供述,并且至今不肯主动交代犯罪事实。
女儿胜利了
12月19日早上9时30分,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。十摄氏度以下的湿冷天气里,多名贵州团的寻亲家长在法院外的行道树上拉上横幅,摆上寻子启事,或把寻子信息印在T恤外穿,或在书包背面印上,在胸前挂上寻子信息,组成一面红色的“墙”。
“妞花加油!愿天下无拐,宝贝回家,加油!加油!加油!”
镜头扫过,每一个寻亲家长都怀揣着一个痛不欲生的故事。他们无一例外地爱杨妞花、恨余华英,仿佛长时间溺在沼泽中的人,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 天气寒冷,寻亲家长在法院门口支起自热锅炸土豆片
天气寒冷,寻亲家长在法院门口支起自热锅炸土豆片
一位阿姨寻找的女儿周君,走失于2003年12月12日,走失地点是贵州贵阳北郊小学门口。女儿在照片里扎着双马尾,笑得灿烂,双眼皮,她面对镜头声泪俱下:“女儿还在的话,应该已经工作了”;一个女儿寻找79岁的母亲李辉,找遍了福利院和救助站;一名头发花白的家长寻找从家门口被拐卖走的儿子,儿子说晚饭想吃腊肉,但还没吃上就被拐走了,“宝贝,不是我们不要你,这21年我们真的很艰难,你快回来”,她说丈夫已含恨而终,儿子可能已经成家,自己不奢望他回家,只想知道“儿子在哪里,还活着吗”。
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天下午,杨妞花知道这次很可能是终审,组织了一场媒体和寻亲团的“简餐”,在媒体的直播面前,她把每一个来到现场的寻亲家长拉到跟前,挨个介绍丢失的孩子,“我希望能抓住最后的流量,帮帮他们。”
寻亲家长们视杨妞花为女儿,墙上的横幅写着:“欢迎女儿回家。”有的寻亲家长天天刷杨妞花的直播,还有的家长特别喜欢杨妞花,就像看到了理想中自己孩子的模样。
 墙上横幅写着“欢迎女儿回家”,寻亲家长们围着杨妞花
墙上横幅写着“欢迎女儿回家”,寻亲家长们围着杨妞花
“这孩子这么漂亮,一看小时候就是养得很好的,绝对不是被家长卖掉的,是人贩子让这么多人骨肉分离。”杨妞花的话也说到了寻子家长心口上——很多被拐的孩子,可能会被养家灌输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思想,从而不愿意寻亲。
“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当庭宣判,二审驳回上诉,维持死刑!”12月19日下午2时许,杨妞花走出法庭,在人群的簇拥中,几乎是嘶吼着宣布上述消息。
等待在法庭外已一上午的寻亲家庭和媒体“炸”了。数十名贵州寻亲团的阿姨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,眼含热泪,举起寻亲启事高喊:“判得好!判得好!”她们说:“女儿胜利了,我们高兴。”
“哪里有流量,我就去蹭”
余华英被判死刑第二天,“棉花糖爸爸”买了纸钱和鞭炮,跟随杨妞花一起回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给父母上坟。他考虑了半天,觉得穿白色的寻亲T恤不太好,穿了一身黑夹克,背上一个黑书包,背面印着女儿走失的信息。
媒体采访杨妞花时,和她拉起家常,有说有笑。他则把黑色的书包背在胸前,露出寻女的信息,沉默地杵在杨妞花背后,一脸严肃。有媒体示意他靠边站,他尴尬地找不到位置。杨妞花自然接过了他的书包,放在了自己面前。
杨妞花上坟时,“棉花糖爸爸”总是抢着干活:或给媒体拿麦、或在一旁撕纸钱、放鞭炮。他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站在杨妞花旁边,争取一个镜头。
2006年10月19日,女儿陈杨梅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南站广场失踪后,“棉花糖爸爸”陈生梨将寻亲启事贴满五菱宏光面包车,开着它全国各地跑,吃住都在车上。寻亲启事上,陈杨梅的照片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拍的。她眼睛大大的,右边太阳穴下有一颗小黑痣。

如今,他已经跑废了几辆面包车,行程几万公里,其他家长的寻亲启事也贴上了,但女儿仍然像掉进大海里的一根针。
“哪里有流量,我就去蹭”,他直白地对记者说,这几年寻亲的流量减少,自己需要“露出”。
 棉花糖爸爸的面包车上贴满寻亲启事
棉花糖爸爸的面包车上贴满寻亲启事
去年贵州村超大火,他和另外几个寻亲家长举着寻亲启事沉默地站在人群中,保安来驱赶、有人指着他骂,他不反抗、不回嘴,换个地方继续举,坚定的眼神被媒体拍下,“棉花糖爸爸”终于“火”了。
“后来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提供线索”,陈生梨很高兴,他更加把希望寄托在流量上,但他补充说:“我们也不是什么流量都蹭,杨妞花对我们好,我们才追着她。”
余华英案重审一审判决时,贵州寻亲团来了一百多号人,有的人“抢镜头”,把寻人启事举到杨妞花前面。寻亲团就定下一个规矩,一律站在杨妞花背后。被人指着鼻子骂“蹭流量”时,陈生梨也不敢回嘴:“我们这样的人,不敢被讨厌。”
杨妞花给父母上坟结束时,陈生梨接到一个来自湖南邵阳的电话提供线索,对方看了杨妞花的直播给他打来,怀疑抱养的女儿可能就是走失的陈杨梅,可是最后期待还是落空:年龄、地点对不上。
 “棉花糖爸爸”接到线索却对不上。
“棉花糖爸爸”接到线索却对不上。
这一天是冬至前一天,路上大雾弥漫。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,诗歌中旅人该早早归家的日子。陈生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,手机里播放着他去年接受采访的视频:“我太需要有个人,把我女儿带回家。”一直在人前陪笑的他,手握着方向盘默默哭了。